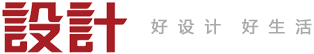張利,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筑師。國際建協理事、國際建協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建筑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總師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22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臺”總設計師。2014至2015年任北京冬奧申委工程規劃部副部長、場館與可持續發展技術負責人、陳述人,2016至2022年任北京冬奧會張家口賽區及首鋼單板大跳臺場館規劃設計總負責人,2020至2021年任第17屆威尼斯國際建筑雙年展中國館總策展人。
學術方向聚焦于設計科學的“城市人因”領域,將結合人因分析的設計干預方法用于冬奧場館的可持續設計,主持了“雪如意”“冰玉環”、首鋼大跳臺等體現中國元素、服務賽后長期利用的冬奧項目。

從群明湖北岸看跳臺
動作觀賞性強、視覺沖擊力大的自由式滑雪大跳臺是目前“冬奧大家族”中最年輕的項目,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競技項目之一,是自由式滑雪大項中的分支,也是7個冬奧會新增設項目之一。自由式滑雪從上世紀中葉開始首先在美國發展起來,九十年代陸續被列入冬奧項目,由雙板完成。自由式滑雪項目包括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型場地技巧、坡面障礙技巧、障礙追逐和大跳臺等小項,不同小項各具特色。
首鋼滑雪大跳臺在設計理念上,借鑒了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元素。之所以能成為北京冬奧會唯一一個設在城區內的雪上比賽場地,原因一是滑雪大跳臺項目是一項深受年輕人喜愛的體育項目;二是選在首鋼工業園區內,可以充分體現北京2022年冬奧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將冬奧文化與首鋼工業遺址完美地融合,打造出東方文化和北京老工業遺址文化完美融合的經典案例。
首鋼滑雪大跳臺在冬奧會后將作為世界首座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臺場館,承辦國內外大跳臺項目體育賽事,作為專業運動員和運動隊訓練場地。正因如此,首鋼滑雪大跳臺在設計、建設之初就充分考慮到賽后的利用。冬奧會后,滑雪大跳臺可以實現迅速“變身”,向公眾開放,成為服務大眾的體育主題公園。在滑雪大跳臺下方的體育廣場和觀眾區,還特別設置了“氛圍照明”系統,未來將給觀眾帶來與傳統賽事完全不同的觀賽體驗,同時也可以舉辦演唱會等大型活動,探索推廣奧運遺產帶動城市更新的發展模式。

出發區鳥瞰
《設計》:規劃之初為何決定在北京市內修建一個大型滑雪跳臺?作為全球首座永久跳臺,選址首鋼園區這個工業遺址上,對于冬奧會競技和賽后利用分別有著怎樣的考量?
張利:滑雪大跳臺這項體育運動大概在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它主要的粉絲群是都市里的年輕人。傳統的活動形式一直在城市中心廣場或城市中心的體育場或其他的事件空間里,用腳手架搭成比賽的跳臺,比賽的現場就像一場大秀,有搖滾樂隊在現場演唱,大家喝著啤酒跳著舞,甚至于有的時候在夏天也能用碎冰鋪就跳臺。在距2018年平昌冬奧會前約兩年的時候,才決定把這項運動加入到冬奧會里。
對于這項運動,組委會一直希望不僅有一個比賽場館,更希望這個冬奧場館最后能夠做成這項運動能夠被大眾永久性識別的一個元素,所以在此次北京冬奧會后,滑雪大跳臺會成為一個永久性的場館保留下來。為了匹配這項運動“炫酷”的特性,北京冬奧組委推薦了首鋼園區,這是一個特別英明的方案,首鋼園區不僅地理位置好,在這里興建場館還能與工業遺產和城市更新的進程連結在一起。
大家在轉播畫面里能看到的那四個大“煙囪”就是原來廠區的冷卻塔,我們沒有做過多的裝飾,只是用200公斤的水槍噴射去除了建筑上長年積累的塵污,露出了混凝土原本的質感。
像任何比賽一樣,大型的器械都有固定的尺寸,但這個比賽的特點是每一次都要做一個不一樣的曲線出來,從加速到起跳到騰空到落地,但每一個賽場加速區的坡度并不完全一樣,在35到40度之間,首鋼這個我們做了37.8度。這個具體的角度是國際雪聯負責計算競賽的專家計算出來的,他會根據運動員起跳時的初速度、騰空的高度、落地的區域、承受的最大撞擊力以及下降的最后能夠減速的曲線形態進行判斷。因為首鋼園區做的是一個永久的跳臺,以前用腳手架臨時搭建的跳臺的落差大概只有40多米,咱們這次做到了53米,是這項運動目前為止最大的跳臺。

仰視跳臺及冷卻塔
《設計》:滑雪大跳臺作為專業賽事場地,建筑的規模和尺度是否有一定之規?留給設計師發揮的余地有多大?最具挑戰性的是哪個部分?
張利:這就好像修火車站,鐵軌就從這兒過,你要給它修一站臺,你說設計師有多大發揮能力的空間?除了要吻合鐵軌的方向,剩下的都是你創作的空間。在這個案例里就是要跟跳臺運動曲線的邏輯相吻合,你做的東西得能用到比賽里,但剩下都是發揮的余地。
在蘇翊鳴得金牌以后,國際雪聯競賽部主任羅伯特·莫雷西(Roberto Moresi)給我打電話,祝賀我說:你這個跳臺給我們整個運動帶來了巨大的人氣。他們之后5年的比賽已經全部被預定完了。在這之前,滑雪大跳臺一直是冬季項目中相對邊緣化的運動,屬于他們一直在極力推廣的小眾運動,現在變得大家都想把這個運動請到他們的城市里去。
老實說這項運動確實刺激又好看,但跟傳統的高山滑雪非常不同。高山滑雪也很刺激,但是跟這個項目是兩回事兒,那廂是北歐式的勇敢,會一絲不茍地訓練,動作要反復訓練才能保證完成得準確。而自由式跳臺滑雪主要是青年人在玩,很有娛樂性,每個人都是特立獨行地追求標新立異。這個年齡段和這些孩子的屬性決定了這項運動對城市中的年輕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設計過程中最困難的部位你可能都不會想到。跳臺本身它當然有很多難的地方,包括怎么讓它結構合理,我們會和長期在北京工作的比利時結構設計師共同探討,他非常善于鋼結構上的創意。但最難的部分其實不是跳臺本身,而是它在場地里怎么放。你可以設想一下,一個斜的大跳臺,你該以什么角度把它放在園區里,讓人從湖對面看老首鋼的天際線時不會產生違和之感?為了找到這個合適的角度,我們做了很多實驗,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它的擺放位置,比如從長安街的沿線看過來,跳臺跟這幾個塔是什么關系。

裁判塔看跳臺
最主要的視角是從首鋼冷卻池對面看過來,畫面中有4個冷卻塔,后邊是西山,這臺子要怎么擱才不會讓人覺得它跟這些建筑、景物有太大的沖突?當中有這么幾個重要的決策,首先是把跳臺的結束區,湖旁邊場地的標高點往下沉了5米,否則53米的跳臺的頂端距離70米高的冷卻塔的高度差就會在10以內,人在地面上的視覺從某些角度看,就會覺得跳臺比冷卻塔高。我們要確保它的高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超出冷卻塔,從冷卻塔的高度順延下來的是一條曲線。第二就是靠科學,我引入了“人因分析方法”,即運用虛擬現實技術,在比賽能夠接受的約四五十度的范圍內,從最朝東南的角度開始,每五度設置一個測試場景,讓不同的人帶上VR眼鏡,在虛擬現實中進行對照觀看,我們則可以追蹤眼球瞳孔關注的地方是哪個點,同時測量皮膚電,基本上就能知道觀者認為哪種情況下跳臺和場景是一體的。這種科學方法比傳統的問卷走訪等方式更真實有效,它可以過濾掉很多主觀因素的影響。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冬奧會設計里大規模采用人因技術。因為我們曾經看運動員做這種測試,測量他們的心率、肌肉壓力等等,我們覺得這個技術完全可以應用到建筑空間中。

跳臺競賽照明夜景
《設計》:為響應了此次冬奧會的綠色主題,首鋼滑雪大跳臺在低碳環保方面做了哪些針對性的具體設計?
張利:對工業遺產再利用,用冬奧場館來帶動區域發展,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這是把已經廢棄的空間還給城市,用新的生活。具體做法有三個,一是我們把賽后用的東西和賽時用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比如跳臺結束區部分,面積有近一公頃,差不多100米×100米那么大的一塊地方,我們做了一個半下沉的空間,大約能容納五六千人,日后可以搭建舞臺做各種各樣的演出,目前已經嘗試用了幾次了,冬奧會的志愿者發布會就是在那里進行的。
此外,設計團隊仿照頤和園里的湖面及建筑的設計理念,將相似的拓撲關系引入到首鋼園的群明湖中來,使滑雪大跳臺成為獨特的視覺吸引點,并創造了一些使人能夠停留下來的欣賞大跳臺的開放空間,如仿照頤和園魚藻軒的視覺觀感,在群明湖西北側方位打造的親水平臺,成為欣賞首鋼滑雪大跳臺、拍照打卡的絕佳位置;又如,景觀設計師還精心設計了縱深到群明湖水里面近距離體察大跳臺的空間,讓人非常欣喜。由此把賽后的文化旅游和賽時的體育比賽的不同使用方法結合起來。

從新首鋼大橋看首鋼園區
第二,是材料本身的可持續性。大跳臺的材料99%是預制的,一共7000多塊,賽場現場除了整理地基外,都是現場搭建工作。這里面的好處就是,鋼結構在碳足跡的計算上比混凝土優秀太多了,因為構件都是在工廠預制好的,現場產生的熱作業就非常少,碳排放很低。當然工廠加工這些構件是需要產生碳排放的,但是這些碳排放在工廠的環境下很集中,單位面積上的碳排放就會降低。這絕對是一個可圈可點的裝配產品。
第三,是對環境的改善。園區原來有1個制氧廠區,那4個冷卻塔是電廠的設施,周邊環境土壤里有有色金屬的沉淀和化學物質的殘留。所以整個園區的改造除了把制氧廠改成將來的文化體育活動空間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用有機植物的物種來治理土壤,吸收有害的離子。景觀設計和環境治理是結合在一起的,而且接近水的好處就是有一些物種長得很快,而且因為地下水位高,植物對離子可以吸收得很快。如果不用這些物種等著環境自然修復的話,徹底修復可能要30~50年,現在這種方法有可能把這個周期縮短到3~4年。

群明湖
《設計》:在“雪如意”和“雪飛天”的設計之初您就考慮到了場館在賽后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多了避免“白象”現象這一重前提的考量,對場館的設計帶來了哪些影響?
張利:首先,它不是完全由競賽工藝決定的,比如奧運會比賽現場都會有六七千人的觀眾,進場要經過安檢等程序,就需要設計路線等配套設施。通常就會想方設法做一大塊平地,然后用護欄圍起來,把競賽設施放到中間。但我們這次不是這么做的,設計完全是從將來這個永久性的設施怎么使用的角度入手,結合既有條件再去放這個設施。思路是反轉的,把競賽看作對常設設施的臨時使用。最初的設想是賽后這個跳臺不會被體育比賽長時間占據,所以更多考慮的是舉辦音樂會、親子旅游等。賽后羅伯托·莫雷西告訴我,好多贊助商愿意回到首鋼來比賽,一旦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相信這個比賽會經常回到這里來,甚至于季節都不是問題。

群明湖東岸看大跳臺傍晚
《設計》:此次設計過程中您嘗試了怎樣的探索和創新?積累了哪些經驗?
張利:最大的一個收獲就是覺得人因分析這個工具以后要常用,不拘于項目的大小。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同行說這個事情,原來我們做設計都是憑感覺,或者說憑經驗做主觀判斷,但遇到我覺得行,你覺得不行的情形,如果你比我經驗豐富,我就得聽你的。但現在有了這個手段,很多時候可以客觀地測試。而且有些情況即使憑經驗也判斷不出來,用技術手段就可以更精確地找到多數人在審美上更容易接受的選項。
畢竟建筑設計只能做一次,不像產品設計的外觀可以根據市場需要隨時調整改版,建筑設計如果失敗了,它也永遠在城市里矗立著,一直被看到。所以,在虛擬的環境底下,在建筑沒蓋起來以前,就有這種接近蓋起來測試來參考。參與測試的人群我們基本上考慮到了不同的背景,當然我們有一個最好的測試人群,就是清華不同院系的學生,他們本來就對新鮮事物感興趣,年輕的群體又是未來城市的主要使用者。但是對特殊的項目,比如像首鋼園區,我們也找到了一些首鋼以前的工人,曾經生活在首鋼的人,來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