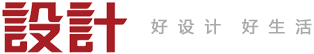羅成 ,浪尖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國家首批高級工業設計師,高級工藝美術師。先后榮獲光華龍騰中國設計貢獻獎金質獎章、“中國設計70人”、中國設計業十大杰出青年、中國“金羊獎”十大設計師、ICIF文化產業英才獎、廣東十大青年設計師等稱號。任職光華龍騰設計創新獎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設計產業聯盟副理事長。受聘為重慶大學、深圳大學、武漢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湖北美術學院、湖北大學、南京工業大學等十多所院校的客座教授、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
“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模式本身就是一個以產業共贏為目標、以行業共享為原則,以協同共創為手段的開放性平臺,我們竭誠歡迎更多工業設計和產業鏈上的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和廣大從業者一起共建這個生態體系,共同推動工業設計的產業化發展進程。羅成認為,設計是建立在知識貫通基礎上的認知賦值,無論是美學、技術、心理學,還是人因工程、材料學,都是“知識”領域的積累,輸出的則是平衡各類知識后的問題解決方案。未來必然是大設計融合的時代,設計師必然要成為創新型、復合型的人才。
《設計》:浪尖的發展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這些階段又反映著中國工業設計怎樣的發展歷程?
羅成:浪尖的發展經歷的三個階段:一是以垂直領域產品創新和價值深挖為特征,以產品級創新為核心的深耕式發展階段;二是以服務領域、產業鏈延伸和全國布局為特征,以產業級創新為核心的開拓式發展階段;三是以全產業鏈平臺搭建和全球布局為特征,以社會級創新為核心的平臺化發展階段。
這三個發展階段與同一時期中國工業設計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我顛倒一個順序,先分析時代背景,再介紹和總結浪尖的階段性發展。因為作為這個時代里的一粒沙,是時代造就了浪尖。
第一個發展階段起步于浪尖的創立,也就是90年代末。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從80年代初以仿制和引進為主的“無設計”狀態中,開始認識到工業設計的重要性,并轉向自主品牌的誕生和壯大。尤其是家電制造業的繁榮,記錄了那個階段中國工業設計的發展和變遷。
1999年浪尖創立之初就提出“平衡的設計理念”,系統性地思考“人、事、理”三者之間的相輔相成,以“合理高效的解決方案”、“產業鏈競爭的共贏模式”、“平臺設計的強大優勢”、“換位思考的共生設計”四大方法(2002年提出)帶領團隊在深圳當時設計創新最活躍的家電、音頻、數碼等產品領域進行深耕,用設計幫助尚處在起步階段的制造業眾多品牌提供價值服務。其中有華為、中興等后來成長為行業龍頭和國際知名的企業,也有不少曇花一現的山寨產品。在服務與被服務的過程中,浪尖的團隊不斷成長、壯大的同時,深刻理解了制造業客戶的多維需求,洞悉了從OEM向ODM和OBM轉型的趨勢。于是我們主動思考、探索,并著手產業鏈布局,于2002年創辦了匯鼎模具。幾百人的模具廠,至今仍以90%以上的國際業務、年均遞增超過20%的速度占據著精密模具領域的中高端市場,為浪尖的服務用戶提供優質配套服務。

北京大興機場自助托運系統
第二個發展階段的時代背景是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本土制造業企業為了與有著優良設計、技術和品質的外國產品競爭,開始將工業設計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與戰略中,紛紛設立設計中心,或將工業設計從原來的企業技術中心獨立出來。另一方面,技術型企業通過科技創新為產品注入競爭力的同時,也強化了對工業設計銜接和協助技術成果轉化的依賴。與此同時,國家對工業設計的重視和在政策上的引導與支持,深圳、無錫等各地涌現出一批工業設計園區,加速產業集聚,助推“中國制造”開始向“中國設計”轉變。
在這個背景下,浪尖的設計服務也從以電子類產品為主,邁向軍工、交通、醫療、文旅等眾多領域,覆蓋衣、食、住、行、游、娛、購等應用場景,并開始了全國布局。在2007-2015年期間,先后在東莞、寧波、成都、香港、鄭州、義烏、上海、蘇州等地成立了浪尖設計機構,依托當地資源稟賦,深耕區域產業發展,迅速成長為當地具有影響力的設計品牌。在此期間,定位于產品研發和供應鏈服務的浪尖科技,定位于創新型復合型人才培養的浪尖學院,定位于文創和IP衍生品開發的浪尖文化,以及定位于設計創新項目孵化和投資的浪尖D+M眾創空間和浪尖資本等也先后創立,浪尖集團以產業鏈的延伸和服務領域的拓展,為下一階段的平臺化、國際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第三個階段也是設計互聯與設計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是數字化技術驅動商業模式創新和產業生態重構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要求工業設計成為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這一重要角色的新時期。此時,中國已經從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國轉變為最大的消費國,工業設計的重心從產品轉向消費者,強調產品的服務屬性和用戶體驗,強調品牌價值的傳遞,強調工業設計的智能化和軟硬件結合。尤其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公共服務領域,移動化場景的社區、旅游、醫療服務正在興起,相關產品創新和模式創新充分體現了大數據與設計的結合。

康復儀器
在這個背景下,浪尖一方面積極整合國際資源,繼續深挖設計價值的創造,與意大利、德國、丹麥、奧地利的家居設計、用戶體驗、服務設計和新材料研發等領域的全球知名機構合作,創建了包括人因工程、用戶體驗研究、CMFT、品牌策略等領域的實驗室和專業機構,引入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為設計和產業賦能;另一方面,浪尖積極踐行早在2010年就提出的“D+”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服務模式,在各地政府的引導和幫助下,分別于2015年、2017和2018年分別在重慶、深圳、武漢等地創建了D+M智造工場、D+M智造體驗館和D+M工業設計小鎮,構建了2B、2C、2B2C的多維工業設計產業生態。在此基礎上,整合和承載全產業鏈的設計創新資源和服務要素,積極開展工業設計領域的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發和設計工具開發;積極開拓產教融合領域的校企合作;積極組織創新創業活動,營造和弘揚設計創新文化;積極參與區域產業發展規劃等。通過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的拓展,實現了D+M平臺和工業服務業生態區的構建,為制造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全球優質資源聯動的強大助力。由此,浪尖的定位從設計機構轉變為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服務運營商。

輸液監護器
《設計》:近四十年來,中國工業設計師這個職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社會對設計價值的認知達到了怎樣的水平?
羅成:看待中國工業設計師這個職業的變化,或者說是職業化發展,必須以中國工業設計的職業化教育和產業化進程為背景,否則就失去了參照和依據。
在教育方面,中國工業設計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末。從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建立物質生產體系,到1979年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的前身“中國工業美術協會”的成立,再到湖南大學、無錫輕工學院(江南大學)、重慶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陸續設立“工業設計”專業……應該說,是中國工業設計教育的職業化和改革開放驅動的物質生產體系建設需求,催生了中國工業設計的職業化發展。
在此之后,在國家政策引導、市場需求和生活美學傳播的多重作用下,眾多工業設計公司和各類機構陸續涌現,各地紛紛成立的工業設計協會組織,為中國工業設計人才的成長和發展提供了平臺和空間,越來越多的藝術、工學、商學、管理學和信息技術等領域的人才走上工業設計的專職崗位。
盡管在中央領導的重視和推動下,廣東省和浙江省陸續實施了高級工業設計師職業資格認定,但是,由于認定條件的設定并未與從業資格接軌,導致與基數龐大的年輕一線工業設計從業人員有很遠的距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給廣大工業設計從業人員帶來自我認可和職業歸屬感,積累一定經驗后的中堅層骨干設計師轉行產品開發、品牌服務或被甲方挖角而結束職業生涯的比例極高。可以說,迄今為止在中國工業設計師這個“稱呼”還沒有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職業背書,這已經嚴重阻滯了中國工業設計師的職業化發展進程。
造成這一現狀的另外一層深刻原因,就是這個話題的后半部分,社會對工業設計價值認知的水平也遠遠未能與工業設計的產業化,以及工業設計師的職業化發展相匹配。剖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工業設計領域長期存在“三個錯配”得不到有效解決,即:工業設計非標定價購買與設計價值長尾顯現之間的“價值錯配”,工業設計在制造業環節中的非必要性角色與產業高水平發展應有的重要地位之間的“角色錯配”,和教育內容、復合型人才培養理念相對滯后的現狀與產業發展對高層次人才需求之間的“人才錯配”,導致工業設計產業化進程滯緩;另一方面,工業設計企業和服務提供機構普遍缺少專業度和核心競爭力,缺少產業鏈的支撐,致使設計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而無法掌控服務交易達成過程中的議價權和設計工作開展上的主動權,仍然存在為迎合客戶而抄襲和提供低水平設計方案的情況;再一方面,以工業設計企業為主體的規上比例很低,行業力量普遍弱小,或各自為政,或依靠幾個長期客戶小富即安不思進取,或掙扎求存疲于奔命,且缺少組織協調,很難在可持續發展上達成共識、形成合力。以上這些都是造成工業設計產業化和工業設計師職業化發展裹足不前的原因。
相比早在20世紀70年代,撒切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期間就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聲音:“工業設計是工業的命脈。英國可以沒有政府,但不能沒有工業設計”,我國政府的重視度很高,但觸及工業設計產業化發展的核心和實質性問題的政策和政策傳導機制還未能建立起來。工業設計在民眾中的認知度很低,對于企業而言,更多的仍處在“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尷尬境地。

電力巡檢機器人
《設計》:浪尖的發展過程中是否面臨過“生死存亡”的時刻?當初是如何化險為夷?
羅成:作為一個經歷了20多年發展的民營企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很多無法想象的困境和在當時看是過不去的坎兒。慶幸的是浪尖有擅于學習和思考的領導和管理團隊,在危機和危險來臨的時候,提前做出研判和規避。當然,也有在發展方向和戰略上謀劃時存在的意見相左,也有在面對是否割舍短期利益、夯實品牌基礎、謀求更長遠發展時候的選擇分歧,但只要問一問當初創建浪尖時的“初心”,所有問題最終都能在發展的大前提下做到決策和行動統一。
所以,我堅定地認為,沉淀和培育良好的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的“韌性”和“張力”,是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區別,是幫助和確保企業能夠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作出正確決策,最終走出困境的依仗。它決定了你能看多遠,走多遠。

服務機器人
《設計》:請您談談您職業生涯中親身體驗到的市場、客戶及用戶的變化。
羅成:工業設計服務的主要客戶是B端的企業,但是企業購買設計服務的目的,最終還是要滿足消費端的真實需求,所以,工業設計其實是先2C再2B的行業,不僅需要關注設計細節、工具、CMF和供應鏈等方面的變化,更需要關注的是整個消費場景的變遷,整個產業和社會生態的變遷。從學了專業入了行業至今,30多年來一直在沒有離開工業設計的一線,也不斷地從與客戶、用戶的接觸和交流中感受市場的變化和趨勢。感受較深的有以下四個方面。
1.在市場變化方面,在從以前的“高頻低價”為主向“低頻高價”為主轉變。本質上,這一轉變是消費升級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以賣方為主導的市場階段,產品生產和供應以滿足功能性需求為主,所以標配的大批量產品流向市場,同時滿足高中低端用戶的共性需要。這個時期,一套模具甚至可以使用很多年。但是隨著產品的豐富,供需雙方地位的變化就要求供給側在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上做出調整,以小批量、個性化來定義消費的細分市場,滿足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審美喜好的群體對產品的需求。與此同時,由于平臺的存在和服務市場下沉,智能化設計、快速原型、3D打印等技術不斷完善,一些C端消費的個人用戶開始定制化購買設計服務和設計產品,促使工業設計服務的購買主體,也在從單一的企業購買向企業與個人用戶同時存在轉變。
2.在設計服務購買訴求方面,在從以前的追求塑造時尚外觀拉動銷量提高市場占有率,向追求結構更加合理、成本更加可控、應用新技術新材料、品質卓越、功能多維等方面轉變。本質上,這一轉變是工業設計從“營銷導向”向“戰略導向”過渡的必然。
3.在設計服務購買方式方面,在從以前的需求方獨擔風險、獨享收益,向供需雙方共擔風險、共享收益轉變。本質上,這是服務交易方式演變升級的必然結果。服務型交易和實物商品交易存在本質上的巨大差別:實物商品在交易環節中是隨著物權的轉移,實現“即購即獲得”;而服務型商品一方面強調過程中的服務體驗,另一方面服務的結果如果是長尾顯現,則帶來的評價和獲得感也將因較長的反饋周期,而無法體充分體現和反映在交易過程中進行評價。這一點在工業設計服務過程中體現得尤為典型。以往相對片面地憑借對品牌的信任和通過服務提供方機構的“賣相”來判斷實力和可信度,都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服務型交易結果滿意度不高的狀況。所以,改變現有“商品化”的工業設計服務購買方式,將設計與產品生命周期、與企業戰略捆綁,創新收益分配方式,構建利益共同體關系,是服務交易模式迭代的必然趨勢。
4.在國家產業政策導向方面,在從以前的培育壯大,向引導和鼓勵搭建工業設計的開放性平臺,加強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和工具開發,促進成果轉化等方面協同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轉變。以國家工業設計研究院為例,《建設指南》中明確提出采取“公司+平臺”的模式,由行業龍頭企業牽頭,以資本為紐帶,整合產、學、研、資等多維資源,在制造業垂直領域構建基礎研究、成果轉化、人才培養等六大功能的開放式平臺的要求。這一點也恰好與浪尖打造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服務體系的發展戰略不謀而合。

蘇泊爾輕量T6手持吸塵器
《設計》:浪尖在業內率先提出并打造的全產業鏈設計創新、D+等理念和平臺樹立了工業設計行業的創新范式,“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模式現已被業內廣泛應用,在眾多追隨者中,浪尖如何保持領先優勢?
羅成:首先,在D+M平臺上踐行的“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模式,是浪尖經過十幾年的摸索,在產業實踐中不斷修正和磨礪出來的,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不僅需要深厚的沉淀和積累,更需要有足夠的規模和資源來支撐高效協同體系的構建。
其次,這一模式從提出到踐行至今,并非處于靜止狀態,而是處于不斷動態調整的過程中。全產業鏈上的每一端,如果要做深、做實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投入,需要對市場、技術、人才、資本等各個方面的變化提前做出洞察和研判。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全產業鏈設計創新”模式本身就是一個以產業共贏為目標、以行業共享為原則,以協同共創為手段的開放性平臺,我們竭誠歡迎更多工業設計和產業鏈上的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和廣大從業者一起共建這個生態體系,共同推動工業設計的產業化發展進程。

登特菲口腔顯微鏡
《設計》:請您從自己的從業經驗出發,談一談設計與品牌的關系。
羅成:究其根本,設計是建立在知識貫通基礎上的認知賦值,無論是美學、技術、心理學,還是人因工程、材料學,都是“知識”領域的積累,輸出的則是平衡各類知識后的問題解決方案。平衡這些知識的原則,就是做設計的價值觀,是提供解決方案的同時,向客戶和消費者所傳遞文化。例如,設計解決方案中使用的是綠色環保材料,那么傳遞的就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文化和價值觀;設計中采用的線條、顏色和元素,也同樣在透過產品表達著哪個語境下與用戶的“文化溝通”。品牌從來都不是自詡的,而是由內而外的標準所傳遞出的,并且能夠被普世認同的價值觀。所以,看待設計與品牌的關系,必須站在文化的層面上,用設計詮釋品牌價值,傳遞品牌文化。

華大基因
《設計》:以AI為代表的高新科技全面“入侵”人類文明,在把人類從繁重的重復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給許多行業帶來了“危機”,甚至已經波及藝術創意領域,您認為設計行業該如何與人工智能共處?
羅成: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在不斷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改變這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其中,人工智能帶來的變化和顛覆最為巨大。近年來,在設計和相關行業中已經有許多人工智能的應用案例,向我們展現出高效和不亞于人類的創造力。但是從事設計工作,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具備很強的學習力。例如,我們幾年前就開始有專人在學習和研究參數化設計,并且在員工中普及培訓,確實給工作效率的提升帶來很大幫助。所以,學習和借助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能夠完成的工作交給它們,把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情做好,是我們重新定位自己、定位設計師和工業設計產業的基礎。

中捷直驅高速五自動電腦平縫機
《設計》:在當下社會,您認為設計師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和能力以應對當今瞬息萬變的商業需求?更好地和產業融合助力企業發展?
羅成:未來必然是大設計融合的時代,一個項目可能是產品、建筑、視覺、環境共同參與設計的,這個過程中需要很多基礎研究和技術的支撐,并且這些研究成果是具備共性指導意義的,可以用在某個運作系統中,也可以是方法和工具應用在很多行業產品中,所以設計師必然要成為創新型、復合型的人才。
《設計》:您想給設計教育提點兒什么建議?
羅成:對教育我一直持敬畏的心態。盡管我們都經過了高等教育,也受益于教育帶來的知識和技能,但是教育永遠面臨著“用當前的課程內容培育未來的人才”的尷尬。因為,身處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我們很難用現在的眼光和認知,去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未來的社會和產業發展的變遷,以及會對未來的人才提出怎樣的要求。
“產教融合”是工業設計全產業鏈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貫徹國家“產教融合”精神,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校企合作,給我們提供了與高等教育緊密合作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將多年來積累和總結的經驗,接觸到的產業發展最新的需求和變化,相關基礎研究領域的突破,創意工具的迭代等內容,通過“三個交互”構建“三個場景”,實現“三個融合”。三個交互是指交互工具、交互課堂、交互實踐;三個場景分別是產品場景、產業場景和社會場景;三個融合是與價值融合、與世界融合、與未來融合。這套“浪尖交互式全景教育TM”體系的構建,我們已經思考和沉淀多年,并且已經開始與國內一本高校實質上開展了合作人才培養,取得了良好的收效。這也是我們對設計教育提出的建議和給出的“浪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