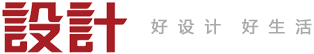南通大學(xué) 吳國強(qiáng)
摘要:當(dāng)代設(shè)計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jìn)程,藝術(shù)實(shí)踐“應(yīng)如此”的向往,經(jīng)由設(shè)計藝術(shù)能動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使設(shè)計倫理成為指向未來的精神擔(dān)當(dāng),不僅體現(xiàn)今天時代的審美價值理想,更激蕩起人們對明天價值倫理的不盡瞻望,為人的生存實(shí)踐和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當(dāng)代設(shè)計 藝術(shù)實(shí)踐 倫理意義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7)11-0043-03
Abstract:Contemporary design is affecting ubiquitously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t an unprecedented depth and bread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art practice should be longing for the ideal. The design art is changing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values, it makes design ethic become spirit undertaking. Not onl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ideal, but also looking forward the value of ethics in the future,it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 practice.
Keywords:Artistic practice Contemporary design Ethic significance
引言
實(shí)踐的本質(zhì)是對目的的追求,目的是整個實(shí)踐活動的起始和歸結(jié)。就藝術(shù)實(shí)踐視域?qū)徱暜?dāng)代設(shè)計,“這一文化性主題圍繞著當(dāng)代人的精神、價值等內(nèi)在維度,它內(nèi)斂地、沉淀地反映著時代的精神狀態(tài),體現(xiàn)著大變革時期人的價值理想的確立與維護(hù)”。[1]這一文化現(xiàn)象足以說明,藝術(shù)不僅是認(rèn)識的,而且是實(shí)踐的;認(rèn)識活動由外部客觀事實(shí)向內(nèi)部主觀意識潛移,而實(shí)踐則由內(nèi)部主觀意志向外部客觀事實(shí)轉(zhuǎn)化,前者體現(xiàn)了客觀感受,后者則是實(shí)現(xiàn)目的的行為過程。也即是說,“理智的工作僅在于認(rèn)識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這世界成為應(yīng)如此。”[2] 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出發(fā),從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層面上將實(shí)踐理解為是“人的感性物質(zhì)活動”,并認(rèn)為,人的生存實(shí)踐為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本文基于這一唯物史觀,就當(dāng)代設(shè)計藝術(shù)實(shí)踐對人價值生存與現(xiàn)代社會文化的倫理意義,展開探賾鉤深。
一、藝術(shù)實(shí)踐的目的指向
藝術(shù)是由人實(shí)踐的,因此,藝術(shù)實(shí)踐的目的也就必然指向人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認(rèn)為就藝術(shù)實(shí)踐范疇而言,宇宙間一切體現(xiàn)藝術(shù)存在的東西都只是藝術(shù)的手段,唯有人才是目的——藝術(shù)需要體現(xiàn)人性價值與尊嚴(yán)的倫理意義。從這樣的認(rèn)識觀出發(fā),藝術(shù)實(shí)踐起到了維護(hù)意義人生、抗衡人在社會進(jìn)步中自我“異化”的作用。以人為“對象”還是以人為“目的”的認(rèn)識差異,形成了認(rèn)識論與實(shí)踐論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shù)觀。“以人為目的”本質(zhì)地揭示了藝術(shù)的實(shí)踐性特征,給予實(shí)踐論藝術(shù)觀以根本性的肯定。
不同于認(rèn)識論藝術(shù)觀追求逼肖再現(xiàn)對象、強(qiáng)調(diào)客體至上的評判準(zhǔn)則,實(shí)踐論藝術(shù)觀認(rèn)為,改造客觀對象使人求得物質(zhì)和精神滿足才是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價值所在。這樣的認(rèn)識觀表明,藝術(shù)實(shí)踐所要實(shí)現(xiàn)的終極目標(biāo),是為了使人獲得物質(zhì)和精神的自由,即依循人所意愿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實(shí)踐論藝術(shù)觀才主張藝術(shù)應(yīng)當(dāng)反映人精神向往的“應(yīng)如此”,而不是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是如此”。一切“應(yīng)如此” 都源自于人對現(xiàn)實(shí)人生“是如此”的意識反應(yīng),正由于人對生活現(xiàn)存“是如此”的質(zhì)疑與不滿足,才因此產(chǎn)生了對超驗(yàn)“應(yīng)如此”的強(qiáng)烈向往。毫無疑問,藝術(shù)實(shí)踐以“應(yīng)如此”深刻地體現(xiàn)了人類生存的精神訴求,本質(zhì)地反映了蟄伏于人類內(nèi)心深處的憧憬與向往,超驗(yàn)地規(guī)約了種種引導(dǎo)人類詩性成長的自我設(shè)定,進(jìn)而引領(lǐng)人們走向“應(yīng)如此”的輝煌明天。
二、藝術(shù)實(shí)踐的價值屬性
如上所述,“以人為目的”本質(zhì)地體現(xiàn)了藝術(shù)的實(shí)踐性特征;與此同時,藝術(shù)對于外界事物反映的主觀性,又決定了這種反映具有建構(gòu)與創(chuàng)造的性質(zhì)。因此,我們對藝術(shù)不能僅從物像的客體角度來認(rèn)識,還需要立足于精神層面,把它“當(dāng)作人的感性活動,當(dāng)作實(shí)踐去理解”。[3]
為此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歷史的出發(fā)點(diǎn)是“從事實(shí)際活動的人”,[4] 因為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便是為維持生存而開創(chuàng)的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這表明作為活動主體的“人”,并不是抽象的“僅僅是一個在思想的東西”,[5] 而是具有物欲、情志和愿望的知、情、意統(tǒng)一的生命體。于是,這便決定了人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活動不僅限于理性邏輯的思維意識,也必然會介入知、情、意的情感意識,其中“是如此”是人對外部存在的認(rèn)知,反映的是事物的客觀屬性,自然科學(xué)研究統(tǒng)屬此種反映形式;而“應(yīng)如此”則是人對事物的評價,反映的是審美主客之間的關(guān)系屬性。藝術(shù)反映了事物對人所產(chǎn)生的價值屬性,便是這后一種反映形式。也就是說,藝術(shù)反映的不是理性認(rèn)知,而是主觀意識的感性評價,所要體現(xiàn)的不是事物的本體屬性,而是事物于人的精神價值。當(dāng)今時代,藝術(shù)實(shí)踐無所不在地體現(xiàn)在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切領(lǐng)域之中,當(dāng)代藝術(shù)已走出純粹意識形態(tài)的遮蔽,轉(zhuǎn)而關(guān)注于經(jīng)濟(jì)與建設(shè)環(huán)境等人類基本生存的現(xiàn)實(shí)景況,藝術(shù)與物質(zhì)的聯(lián)系因此而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人們?yōu)樽约旱淖?/span>宅、著裝以及一切生活物質(zhì)存在尋求藝術(shù)呈現(xiàn),在人類的一切日用品中,我們都感覺到了藝術(shù)的存在與設(shè)計的價值。當(dāng)人們衣食無憂具有了“發(fā)現(xiàn)”美的安逸興致時,在藝術(shù)“審美的眼光里,感性形態(tài)無不空靈完美,尋常山石景致也頗顯新奇神韻。在審美逸致的遐游中,主體不免越過藝術(shù)世界的畛域到哲學(xué)的領(lǐng)土上去渺渺于懷,慨嘆天淡云閑,萬事浮埃,千載悠悠”。[6] 藝術(shù)審美使情感凈化提升了人類的心靈,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shù)的最高成就在于它養(yǎng)育和滋潤了人類多如繁星的情感意象。由此可以說,語言的極限遠(yuǎn)非是世界的極限,藝術(shù)的極限才遍及了世界的邊界——藝術(shù)開啟了人與自然的對話之門,自然科學(xué)歸根到底仍然是人同大自然對話的藝術(shù),人提問,大自然回答。在物質(zhì)的有限世界里,人的生命如流星瞬逝匆忙而淡泊,人人都會在意慰藉心靈的共振磁場,無不顧及藝術(shù)審美中的精神向往,人類需要藝術(shù)的滋養(yǎng)。藝術(shù)反映的,正是這種人對情感價值取向“應(yīng)如此”的向往。藝術(shù)的這種精神價值屬性告訴我們,無論作品以怎樣的形式呈現(xiàn),藝術(shù)所反映的必然都是社會倫理價值的評價與選擇。人對于藝術(shù)的向往與追求,能動地推動著人類按照藝術(shù)所隱喻的目標(biāo)去行為,藝術(shù)因而具有了廣義的人生實(shí)踐性質(zhì)和無可替代的倫理價值意義。
可見,藝術(shù)不僅具有補(bǔ)償與安撫人類精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召喚和引導(dǎo)人類心靈成長的價值意義。藝術(shù)實(shí)踐實(shí)現(xiàn)了這樣的傳遞與交流,推動了個體人對社會生活的介入,使之作用于社會的變革與進(jìn)步。也就是說,現(xiàn)實(shí)社會中并不存在著完整的真、善、美,而藝術(shù)“應(yīng)如此”的超驗(yàn)性,向世人昭示了真、善、美的存在且為之神往。于是,由人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反過來影響和改造人的價值取向與生活觀念,成為評判和改造社會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tài)利器。不論是個體人還是人類整體,人之所以能戰(zhàn)勝種種逆境與磨難不斷進(jìn)步,正是因?yàn)槿祟惪偸潜徊粩喈a(chǎn)生的希望招喚和引領(lǐng),藝術(shù)正是產(chǎn)生這種希望和引領(lǐng)的不竭源泉。藝術(shù)的“使命是使一個農(nóng)民作完艱苦的日間勞動,在晚上拖著疲乏的身子回來的時候,得到快樂、振奮和慰藉,使他們忘卻自己的勞累,把它的磽瘠的田地變成馥郁的花園”,并“同圣經(jīng)一樣培養(yǎng)他們的道德感,使他們認(rèn)識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權(quán)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氣,喚起他對祖國的愛。”[7]
總之,藝術(shù)超驗(yàn)的美感不僅使我們在紛亂的人生中獲得了精神的補(bǔ)償和撫慰,其鼓舞人心的真、善、美,還潛移默化地凈化了我們的心靈,提升了我們的人格,指引我們對自己的人生路向做出正確的抉擇。藝術(shù)實(shí)踐對于人具有為科學(xué)技術(shù)所不能取代的精神力量,由于藝術(shù)的召喚,人才有足夠的勇氣掙脫當(dāng)下的人生糾葛,使自己具有了超驗(yàn)的夢想與想象,才可能啟始真正意義上的人性生活。
三、當(dāng)代設(shè)計藝術(shù)實(shí)踐的社會倫理意義
綜上所述,藝術(shù)實(shí)踐是人類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和價值判斷的永恒法則,放眼當(dāng)下時代藝術(shù)實(shí)踐領(lǐng)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dāng)代設(shè)計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作用,設(shè)計藝術(shù)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影響著人類社會進(jìn)程和人性倫理的價值實(shí)現(xiàn)。
物質(zhì)先于意識,任何精神文化無不都是實(shí)時社會生產(chǎn)等物質(zhì)形態(tài)的必然產(chǎn)物。稍加觀察便不難發(fā)現(xiàn),設(shè)計作品承載的絕不只是奉獻(xiàn)給接受者個體的價值體驗(yàn),它更飽含了整體人類社會文化價值之下的審美評判,由藝術(shù)“應(yīng)如此”超驗(yàn)昭示的真、善、美,正存在于被設(shè)計物化的物質(zhì)之中。尤其在社會變革轉(zhuǎn)型時期,物質(zhì)對于精神的影響作用也就愈加明顯。回顧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歷史,社會物質(zhì)結(jié)構(gòu)的每一次進(jìn)步與改變,都可能引發(fā)一場意識形態(tài)的震蕩。曾幾何時,物質(zhì)炫耀曾喧囂塵上,資源消耗與環(huán)境污染成為形影相隨的孿生怪胎裹挾著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度的包裝、海量的攀比消費(fèi)、無休止夸大的商品宣傳,充斥可能為人感官所及的每一時空領(lǐng)域;急功近利、巧取豪奪的“設(shè)計”行為,被冠之以“現(xiàn)代思維”、“全新設(shè)計理念”的美譽(yù),夜以繼日地現(xiàn)身于光怪陸離的醉生夢死場景之中;設(shè)計倫理,成為僅存于利益烈焰灼烤之下的冰山一隅。在這一時刻,“人”不再崇尚內(nèi)心世界的精神向往,“物”卻對人施展著無與倫比的魔性力量:它誘導(dǎo)出種種難以自制的物欲沖動和厚顏無恥的貪得無厭,那些因社會分工所致的工作“權(quán)利”,也蛻變?yōu)槿?/span>性貪婪的邪惡幫兇,所向披靡地施展著不可一世的“物”性魔力。所有這些社會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拜金”丑行,不斷演繹成大大小小“千姿百態(tài)”的“蒼蠅”與“老虎”,猶如鉆出所羅門魔禁的撒旦,肆虐地挑戰(zhàn)著人性的尊嚴(yán),試圖將人的價值理想逼向永無天日的邪惡深淵。但事物總是物極必反的,在物質(zhì)魔欲肆虐登峰造極之時,必然會引發(fā)“漁翁”良知的覺醒,人性貪婪的惡魔終被重囚于所羅門的禁瓶之中。
其實(shí),我們無庸質(zhì)疑人類的精神屬性,人類的天性從不懾服于物性的邪惡,亦不會僅滿足于對自然物質(zhì)的統(tǒng)攝,人性總會本真地以“應(yīng)如此”的超驗(yàn),自覺指引自己去追求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精神屬性,總是樂意在“物性”的層面上獲取更多精神屬性的可能性。抑或設(shè)計藝術(shù)正是為此而產(chǎn)生的,正是設(shè)計藝術(shù)幫助人類最直接地探索與獲取了這樣的精神自由。當(dāng)我們滿懷喜悅地為一件適用美觀的產(chǎn)品而感動時,美的愉悅總會激蕩我們心靈的感應(yīng)力;深諳商道的“誠品”卻不為“商學(xué)院邏輯”所動,連續(xù)賠本15年仍堅持以書店、畫廊和藝術(shù)空間,為寶島居民提供“善、愛和美的素養(yǎng)”,并至死不渝[8] 。這樣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實(shí)踐”事件,必然由衷地使我們感受到了真、善、美的存在,總會激發(fā)起我們內(nèi)心精神活力的增長,使我們對詩性生存充滿了虔誠地憧憬與向往。毫無疑問,正是這種涌動于人內(nèi)心審美愉悅的巨大推動力,成就了人類一路前行的進(jìn)化與發(fā)展。這樣的藝術(shù)實(shí)踐觀,正是“以人為目的”藝術(shù)實(shí)踐論的生動體現(xiàn)。
由此可見,設(shè)計藝術(shù)的倫理意義在于設(shè)計所創(chuàng)造的實(shí)用與審美的雙重價值,它本質(zhì)地反映了藝術(shù)實(shí)踐所蘊(yùn)涵的現(xiàn)實(shí)性與可能性。
當(dāng)設(shè)計物使用功能的現(xiàn)實(shí)物性得到滿足之后,人類又總會向設(shè)計物的現(xiàn)實(shí)“物”性索取更多精神屬性的可能性,這個精神屬性的可能性,即是引領(lǐng)人類一路前行踐行“應(yīng)如此”的倫理意義。黑格爾曾以一名小男孩作為人類自身的隱喻,本質(zhì)而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蟄伏于人心底、引導(dǎo)人類走向成長的本真力量。故事主人公隨手往池水里扔了一粒石子,當(dāng)看到水面不斷擴(kuò)大的層層漣漪時,他為之興奮不已,在驚詫與興奮之余前所未有地體驗(yàn)到了自己力量的作用。毫無疑問,哲人并無意講述一個有關(guān)視覺現(xiàn)象的故事。他只想告訴我們,人在創(chuàng)造出物質(zhì)形態(tài)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黑格爾在這里詮釋的是“人”、“生存實(shí)踐”的意義,故事反映的是主客體之間的關(guān)系,即“漣漪”這一事物對“人”所產(chǎn)生的、由感性評價與主觀意識所引發(fā)的價值判斷,是人情感價值取向“應(yīng)如此”的覺醒。毫無疑問,由此產(chǎn)生的對自我力量的向往與追求,將能動地推動我們按故事所隱喻的目標(biāo)去行為。黑格爾故事所隱喻的,正是人類藝術(shù)實(shí)踐所具有的巨大倫理價值。
人的倫理價值取向是人主體所表現(xiàn)的關(guān)于價值選擇的意識動態(tài),它隨著所處時代環(huán)境等諸多因素的變化而變化,既遵循于人自身思想意識的邏輯合理性,也依托于社會時代的文化價值變遷。當(dāng)前國家崛起的宏大敘事主要體現(xiàn)了科技與經(jīng)濟(jì)的社會物質(zhì)現(xiàn)代化,當(dāng)一個初具溫飽的民族一躍成為為人矚目的經(jīng)濟(jì)大國,在它迅猛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無疑需要精神價值和社會文化的現(xiàn)代化。實(shí)現(xiàn)“社會現(xiàn)代化”并不等同于同步實(shí)現(xiàn)了社會“文化現(xiàn)代化”,哈貝馬斯早就提醒我們,“社會現(xiàn)代化”主要體現(xiàn)為經(jīng)濟(jì)與國家現(xiàn)代化;而“文化現(xiàn)代化”則更多反映了社會物質(zhì)現(xiàn)代化之后人的普遍價值取向。雖然優(yōu)越的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也會水漲船高地促進(jìn)人價值理想的提升,社會現(xiàn)代化也會喚呼與之相應(yīng)的文化現(xiàn)代化出現(xiàn)。然而“文化現(xiàn)代化”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代表一個時代價值取向的現(xiàn)代文化,必然需要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形成過程,只有在人們普遍感知社會新生動態(tài)并經(jīng)歷心理反饋之后,“文化現(xiàn)代化”方會逐漸形成。近年央視“文明就在我們身邊”、“爸爸的謊言”等連綿不斷的公益廣告,正是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審美理想是形成“文化現(xiàn)代化”的先鋒與號角,設(shè)計藝術(shù)責(zé)無旁貸地肩負(fù)著創(chuàng)造審美現(xiàn)代化的重要職責(zé)。當(dāng)社會發(fā)展而文化心理主張意識形態(tài)自主發(fā)展的時候,這就意味著既有社會道德與審美理想標(biāo)準(zhǔn)的動搖。在這樣的社會態(tài)勢中,設(shè)計藝術(shù)便不能僅關(guān)注于本已熟悉的創(chuàng)造語境,更需要關(guān)注所有發(fā)展中的審美心態(tài),需要關(guān)懷更多當(dāng)代人的現(xiàn)實(shí)內(nèi)心,需要更加開放地探索和滿足更為寬廣的人性空間。只有這樣,設(shè)計藝術(shù)才可能擔(dān)當(dāng)起體現(xiàn)并引導(dǎo)當(dāng)代人性價值理想的歷史重任。
在設(shè)計藝術(shù)的實(shí)踐活動中,我們由衷地感到,高度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物質(zhì)成就并不等同于高度文明的現(xiàn)代社會文化;市場經(jīng)濟(jì)強(qiáng)大驅(qū)動力所生成的普遍社會意識,也不能一蹴而就便與農(nóng)耕文明的傳統(tǒng)徹底融合,使之即刻成為當(dāng)代國人的倫理準(zhǔn)則。現(xiàn)代中國所要求的社會現(xiàn)代性并不只是高度發(fā)展的物質(zhì)性,社會現(xiàn)代化亟待文化現(xiàn)代化與之?dāng)y手并進(jìn)。實(shí)質(zhì)上,文化現(xiàn)代化的本質(zhì),正在于對所有社會文化的兼容、傳承與創(chuàng)新,人類歷史與文化一如匯聚大海的江河,文化現(xiàn)代化一路向東的奔騰激流盡管迂回曲折,但不會因?yàn)槿魏卧?/span>滯留在人類文化進(jìn)程的任何階段。“盡管后現(xiàn)代主義產(chǎn)品設(shè)計以調(diào)侃、叛逆、輕松的奇思妙想,極大地豐富了我們時代的生活景象,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一種旺盛的生機(jī)和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人性化時代。相比品味清高,嚴(yán)謹(jǐn)而刻板的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后現(xiàn)代設(shè)計像小學(xué)校園里課間十分鐘自由活動的孩子們一樣,任意揮霍著他們無限充沛的活力與無與倫比的靈動,游戲的淋漓盡致、洋洋得意;然而,后現(xiàn)代繼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勃發(fā)之后的路程并不很長,就像課間自由活動的時間不會很長一樣,后現(xiàn)代社會很快就引來了知識信息時代”,[9] 毫無疑問,“文化現(xiàn)代化”終將在“社會現(xiàn)代化”的呼喚中如期到來。
人類社會總是一如既往地向前發(fā)展著,“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現(xiàn)實(shí)性只能表現(xiàn)為時代性與永恒性的交匯”,現(xiàn)代是‘從短暫中抽取的永恒’;現(xiàn)代不能僅僅為過去與當(dāng)下負(fù)責(zé),現(xiàn)代要‘面向未來,決定現(xiàn)在,并左右著我們對過去的把握。’”[10]哈貝馬斯站在西方文化的基點(diǎn)上,認(rèn)定文化“現(xiàn)代性”首先“是一種個人自由的表現(xiàn),即作為科學(xué)的自由,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任何觀點(diǎn)如果不能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話,其標(biāo)準(zhǔn)斷難獲得認(rèn)同接受,這也是當(dāng)代人作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自由。”[11] 在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指的是獨(dú)立和獨(dú)特的個性品格,注重個體目標(biāo)、個人愿望和個人造詣,注重自我培養(yǎng)和自我身份的確認(rèn)。也就是說,西方“個人主義”強(qiáng)調(diào)的是個體性與差異性,它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意味著人是一切價值衡量的中心,個體人本身就是具有最高價值的目的,社會只是個人的集合體,每個人都是自我約束、自我包容且理論上自足的實(shí)體。可以認(rèn)為,“個人主義”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標(biāo)志,也因此成為西方社會發(fā)展一種至關(guān)重要的源動力。但在中國社會文化中,“個人主義”則是對立于社會群體的個人利益標(biāo)準(zhǔn),無疑是易于渙散整體社會意志的不穩(wěn)定因素。當(dāng)前,厭倦宏觀事物與理想話語、追崇自身日常生活和生理感覺快感、放任個體心理情緒的非目的性的隨機(jī)生活方式,在年輕一代中悄然滲透并一度成為文化流行。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有關(guān)對“個人主義”理解的文化差異所致。這種基于文化差異對個體生存方式的差異化追求,在西方青年群體意識中有著更多個人實(shí)現(xiàn)的強(qiáng)烈愿望,而在我國部分青年群體意識中,缺失的正是對個人成就的迫切向往。
因此,當(dāng)代設(shè)計藝術(shù)需要成為中西不同社會文化與精神理念的溝通媒介,設(shè)計藝術(shù)需要傾力培養(yǎng)社會公眾差異化的審美情趣,使人們理解各自文化的差異性的社會價值所在,在當(dāng)代設(shè)計“百花齊放”的藝術(shù)審美中,獲得自我價值的實(shí)現(xiàn)。由此足見,鑒于東西方種種的差異性意識,謹(jǐn)慎地對待社會轉(zhuǎn)型時期人性存在的矛盾與問題,以歷史使命感“使這個世界成為應(yīng)如此”,是當(dāng)代中國設(shè)計藝術(shù)莊嚴(yán)的社會責(zé)任與至高無上的倫理準(zhǔn)則。
結(jié)語
綜前所述,藝術(shù)實(shí)踐“應(yīng)如此”的向往,能動地推動了人們按它所隱喻的目標(biāo)去行為,因而藝術(shù)具有了廣義的人生實(shí)踐性質(zhì),也因此產(chǎn)生了個體人對社會生活的介入,使社會變革成為可能。由此可以說,作為評判和改造現(xiàn)實(shí)社會人生的意識利器,設(shè)計藝術(shù)能動地影響和改造著人類的生活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有別于傳統(tǒng)倫理觀,設(shè)計藝術(shù)的倫理精神是一種指向未來的倫理責(zé)任。設(shè)計藝術(shù)的倫理作用,正在于它能夠影響我們“使得這世界成為應(yīng)如此”。為此,設(shè)計藝術(shù)不僅需要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短暫的因果聯(lián)系,還需要傾注于未來發(fā)展更為宏觀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也即是說,當(dāng)代設(shè)計不能僅停留在弘揚(yáng)今天時代的藝術(shù)倫理階段,它還需要喚醒人們對明天倫理理想的憧憬與瞻望。“在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關(guān)系席卷全社會,物質(zhì)欲求與精神依恃失衡,導(dǎo)致人性價值匱乏”之時,設(shè)計藝術(shù)實(shí)踐“需要擔(dān)當(dāng)起準(zhǔn)確體現(xiàn)和正確引導(dǎo)人性價值理想的歷史重任”[12] ,當(dāng)代設(shè)計藝術(shù)也因此具有了無可替代的倫理影響價值。
參考文獻(xiàn)
[1] 吳國強(qiáng)著 . 感悟美學(xué)——設(shè)計師的美學(xué)視野 [M] . 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07:165,2,166,166,168
[2] 黑格爾著小邏輯 [M]. 商務(wù)印書館第,1980:420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 [M]. 人民出版社,1960: 6-8、30
[4] 笛卡兒著,龐景仁譯第一哲學(xué)沉思集 [M]. 商務(wù)印書館,1996:126
[5] 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shù)第四卷 德國的民間故事書[M]. 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66:401
[6] 吳清友:我與誠品書店25年[DB/OL].[2017-07-19].鳳凰網(wǎng)資訊 >臺灣 >正文http://news.ifeng.com/
a/20170719/51454647_0.shtml
[7] 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的地平線 [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2